今天是沈从文(1902.12.28—1988.5.10)诞辰。这位从湘西凤凰走出来的“乡下人”,曾被诸多评论家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,也是最早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。他的小说就像家乡山水,清透又有力。
著名画家、作家黄永玉曾经撰写《太阳下的风景——沈从文与我》一文,将自己的流浪经历与表叔沈从文的交往交织在一起,勾勒出一个真实而丰富的沈从文形象。该文收入文景新出《太阳下的风景》一书中,现摘录片段,追思故人。

太阳下的风景——沈从文与我
黄永玉/文
从十二岁出来,在外头生活了将近四十五年,才觉得我们那个县城实在是太小了。不过,在天涯海角,我都为它而骄傲,它就应该是那么小,那么精致而严密,那么结实。它也实在是太美了,以致以后的几十年我到哪里也觉得还是我自己的故乡好;原来,有时候,还以为可能是自己的偏见。最近两次听到新西兰的老人艾黎说:“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,第一是湖南凤凰,第二是福建的长汀……”他是以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六十年的老朋友说这番话的,我真是感激而高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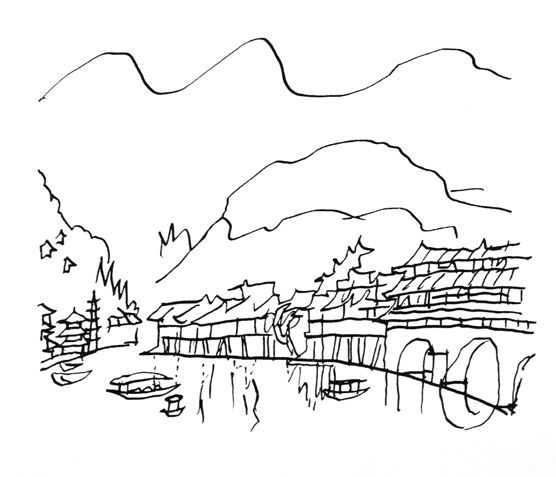
黄永玉笔下的凤凰
我那个城,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洼里。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,有一些峡谷,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,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住。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,有一座大桥,桥上层叠着二十四间住家的房子,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,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,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弯,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,盖了一座万寿宫,宫外左侧还点缀一座小白塔。于是,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。
城里城外都是密密的、暗蓝色的参天大树,街上红石板青石板铺的路,路底有下水道,蔷薇、木香、狗脚梅、橘柚,诸多花果树木往往从家家户户的白墙里探出枝条来。关起门,下雨的时候,能听到穿生牛皮钉鞋的过路人叮叮叮地从门口走过。还能听到庙中建筑四角的“铁马”风铃叮叮当当的声音。下雪的时候,尤其动人,因为经常一落即有二尺来厚。

有一天傍晚,我正在孔庙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进行一场简直像真的厮杀的游戏,忽然一个孩子告诉我,你们家来了个北京客人!
我从来没亲眼见过北京客人。我们家有许许多多北京、上海的照片,那都是我的亲戚们寄回来让大人们觉得有意思的东西,对孩子来说,它又不是糖,不是玩意,看看也就忘了。这一次来的是真人,那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事。
这个人和祖母围着火炉膛在矮凳上坐着,轻言细语地说着话,回头看见了我。
“这是老大吗?”那个人问。
“是呀!”祖母说,“底下还有四个咧!真是旺丁不旺财啊!”
“喂!”我问,“你是北京来的吗?”
“怎么那样口气?叫二表叔!”祖母说,“是你的从文表叔!”

沈从文
我笑了,在他周围看了一圈,平平常常,穿了件灰布长衫。
“嗯……你坐过火车和轮船?”
他点点头。
“那好!”我说完马上冲出门去,继续我的战斗。一切一切就那么淡漠了。
几年以后,我将小学毕业,妈妈叫我到四十五里外的外婆家去告穷,给骂了一顿,倒也在外婆家住了一个多月。有一天,一个中学生和我谈了一些很深奥的问题,我一点也不懂,但我马上即将小学毕业,不能在这个中学生面前丢人,硬着头皮装着对答如流的口气问他,是不是知道从凤凰到北京要坐几次轮船和几次火车?

沈从文
他好像也不太懂,这教我非常快乐。于是我又问他:知不知道北京的沈从文?他是我爸爸的表弟,我的表叔。
“知道!他是个文学家,写过许多书,我有他的书,好极了,都是凤凰口气,都是凤凰事情,你要不要看?我有,我就给你拿去!”
他借的一本书叫作《八骏图》,我看了半天也不懂,“怎么搞的?见过这个人,又不认得他的书?写些什么狗皮唠糟的事?老子一点也不明白……”我把书还给那个中学生。
“怎么样?”
“唔、唔、唔。”
许多年过去了。

黄永玉
我流浪在福建德化山区里,在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。我还不明白世界上有一种叫作工资的东西,所以老板给我水平极差的三顿伙食已经十分满足。有一天,老板说我的头发长得已经很不成话,简直像个犯人的时候,居然给了我一块钱。我高高兴兴地去理了一个“分头”,剩下的七角钱在书店买了一本《昆明冬景》。
我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。钻进阁楼上又看了半天,仍然是一点意思也不懂。这我可真火了。我怎么可以一点也不懂呢?就这么七角钱?你还是我表叔,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呢?七角钱,你知不知道我这七角钱要派多少用场?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过?我可怜的七角钱……
德化的跳蚤很多,摆一脸盆水在床板底下,身上哪里痒就朝哪里抓一把,然后狠狠往床下一摔,第二天,黑压压一盆底跳蚤。
德化出竹笋,柱子般粗一根,山民一人抬一根进城卖掉买盐回家。我们买来剁成丁子,抓两把米煮成一锅清粥,几个小孩一口气喝得精光,既不饱,也不补人,肚子给胀了半天,胀完了,和没有吃过一样。半年多,我明白大腿跟小腿都肿了起来,脸也肿了;但人也长大了……
几十年来,他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,没有这个习惯。当他得意地提到有限的几次宴会时——徐志摩、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,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一次,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。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。那些日子距今,实际上已有半个世纪。

沈从文与张兆和
借用他自己的话说:
“美,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……”
什么力量使他把湘西山民的朴素情操保持得这么顽强。真是难以相信,对他自己却早已习以为常。

黄永玉
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学的工作一定,很快地找到了住处,是在北京东城靠城边的一个名叫大雅宝的胡同,宿舍很大,一共三进院子,头一间房子是李苦禅夫妇和他的岳母,第二间是董希文一家,第三间是张仃夫妇。然后是第二个院子,第一家是我们,第二家是柳维和,第三家是程尚仁。再是第三个院子,第一家是李可染,第二家是范志超,第三家是袁迈,第四家是彦涵,接着就是后门了。院子大约有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孩子。一来我们是刚从香港回来的,行动和样子都有点古怪,引起他们的兴趣;再就是平时我喜欢跟孩子一道,所以我每天要有一部分时间跟他们在一起。我带他们一道玩,排着队,打着扎上一条小花手绢的旗帜上公园去。现在,这些孩子都长大了,经历过不少美丽和忧伤的日子。直到现在,我们还保持了很亲密的关系。

沈从文
我搬家不久,从文表叔很快也搬了家,恰好和我们相距不远,他们有三间房,朝南都是窗子,卧室北窗有一棵枣树横着,映着蓝天,真是令人难忘。
儿子渐渐长大了,每隔几天三个人就到爷爷家去一趟。爷爷有一具专装食物的古代金漆柜子,儿子一到就公然地面对柜子站着,直到爷爷从柜子里取出点什么大家吃吃为止。令人丧气的是,吃完东西的儿子马上就嚷着回家,为了做说服工作每一次都要花很多工夫。
从文表叔满屋满床的画册书本,并以大字报的形式把参考用的纸条条和画页都粘在墙上。他容忍世界上最噜苏的客人的马拉松访问,尤其仿佛生怕他们告辞,时间越长,越热情越精神的劲头使我不解,因为和我对待生熟朋友的情况竟如此相似。
有关民族工艺美术及其他艺术史学的著作一本本出来了,天晓得他用什么时间写出来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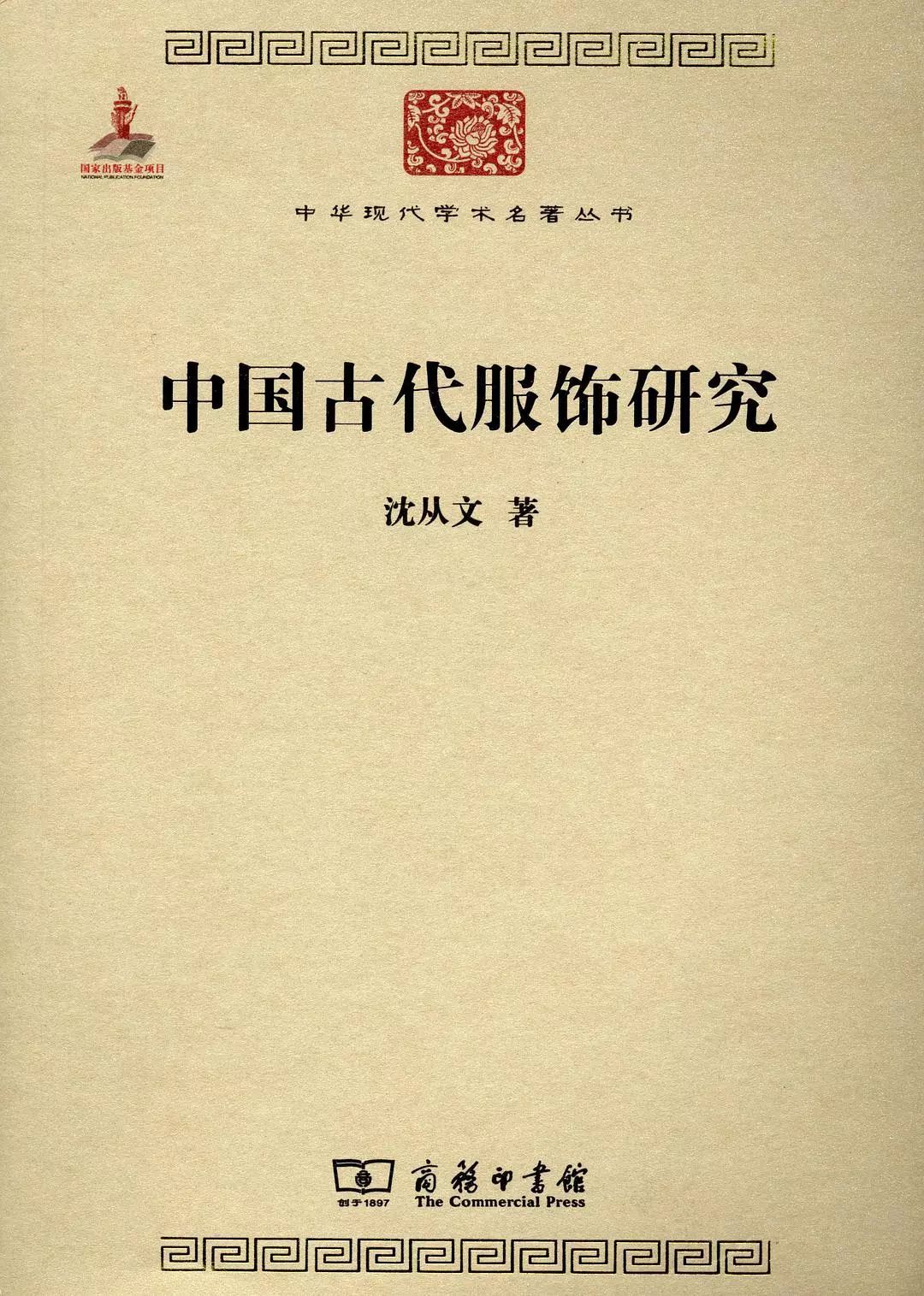
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
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,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,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,真是神奇之至。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,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。没有婶婶,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,又要严格,又要容忍。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,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。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,所以形成一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。婶婶很喜欢听我讲一些有趣的事和笑话,往往笑得直不起身。这里有一个秘密,作为从文表叔文章首席审查者,她经常为他改了许多错别字。婶婶一家姐妹的书法都是非常精彩的,但她谦虚到了腼腆的程度,面对着称赞往往像是身体十分不好受起来,使人简直不忍心再提起这件事。

沈从文与黄永玉
那时候,《新观察》杂志办得正起劲,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刻一幅木刻插图。那时候年轻,一晚上就交了卷。发表了,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,不好看。为这幅插图,表叔特地来家里找我,狠狠地批了我一顿:
“你看看,这像什么?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?你已经三十岁了。没有想象,没有技巧,看不到工作的庄严!准备就这样下去?……好,我走了……”
给我的打击是很大的。我真感觉羞耻。将近三十年,好像昨天说的一样,我总是提心吊胆想到这些话,虽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。
契诃夫说过写小说的极好的话:
“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。”这几乎是搞文学的基本规律和诀窍,也标志了文学的深广度和难度。
从文表叔的书里从来没有——美丽呀!雄伟呀!壮观呀!幽雅呀!悲伤呀!……这些辞藻的泛滥,但在他的文章里,你都能感觉到它们的恰如其分的存在。
他的一篇小说《丈夫》,我的一位从事文学几十年的,和从文表叔没见过面的前辈,十多年前读到之后,深受感动,他说:
“……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,‘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’。”
…………

1982 年,邀从文表叔表婶到凤凰白羊岭黄家祖屋小住(左起:从文表叔、梅溪、永前、永厚、永玉/黑妮 摄)
跟表叔的第三次见面是最令人难忘的了。经历的生活是如此漫长、如此浓郁,那么彩色斑斓;谁也没有料到,而恰好就把我们这两代表亲拴在一根小小的文化绳子上,像两只可笑的蚂蚱,在崎岖的道路上做着一种逗人的跳跃。
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,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。从历史角度看来,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,以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,顺着小河,穿过洞庭去“翻阅另一本大书”的。
拓展阅读
黄永玉:天真如故,乡梦未休
《太阳下的风景》
黄永玉 著
诗书画皆精的大家,
真正有趣的老灵魂
刁钻谐趣,神来妙笔,
勾画漫长而浓郁的崎岖人生
图文原载于搜狐号世纪文景,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有侵权,请联系管理员删除。



